回复1条
-
这个我是同意的。
倒是想到,这里可能涉及到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理工科生往往会像你这么建立模型,假设社会架构是不变的并直接接受主流认知,所关注的差距和可以改变的领域体现在一个个的“项目”。而像我这种教育背景的人,对后者看不懂,但会潜意识觉得前者是可变的,关注的差距和可改变的领域更容易停留在社会不平等、腐败、被政策伤害的群体、实际上广泛存在但在主流认知中被淡化的阴暗面和不良现象等。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曾经是长期经不起这样的关注的,只要去盯一个细节,很容易就能发现大量让人丧气的事情,让人质疑“逐个赶超项目”这样的工程式的模型本身方向就不对。在这种状态下,教条迷信西方乃至不同程度的逆向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就会占据上风,如果当时人在海外,直观感受到方方面面的巨大差距,这种体验会更明显。
实际上的我比晨大晚出生三十多年,出生在碰巧没有下岗的东北工人家庭,从小在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中长大;而如果我最后有机会出国深造,之前就必定和我爱人走到一起并共享他的价值观(否则我的智商大概在当时的高考中相当于一本线高几分。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存在对我造成的激励,可以认为我压根考不上大学),因此我个人碰巧并没有遇到上面我自己假设的局面。但推广到国内的整个人文社科系统,在从90年代至今的几十年中也大致在正常运转,绝大部分人呆在体制内自己的位置上拿工资,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搞到普遍的公开造反、到处逃亡、大量和国安部门互相对线的程度,但这也意味着坐在那些位置上的人普遍有些“计划外”的心态,上课让学生关手机被认为是一种有正义感、学风高尚、不趋炎附势同流合污的表现。这也不奇怪,大多数美国人对自己国家普遍的人文社科自信在建国一百二三十年后才树立起来,之前很多是觉得虽然自己国家的体制是个奇葩,但人都流浪到美洲来了,将就着过吧。今天的典型拉美人仍然是这种心态,作为国家,一辈子没能跨过崇拜“西方”(欧洲)文科理念的这个坎。
以前这些问题其实是都被忽略或淡化了。但在国家进一步的发展中,文科心态上的问题最终是需要解决的。
热点
- 1 过于高估世界的平均水平 18.7万
- 2 初中教材删除康乾盛世 14.7万
- 3 苹果让中国强大起来? 11.3万
- 4 车停桥下躲冰雹致拥堵 8.8万
- 5 F-35差点被击落 18.4万
- 6 回成都开面馆能成吗 11.5万
- 7 如何带领印度走出战败? 2.7万
- 8 日本路边不种树才对? 5.6万
- 9 歼10的艰苦研发过程 6万
- 10 年轻人可能爱上茅台吗? 2.3万
站务
-
请你来预测,2025年这些期待是否会发生?
岁月匆匆,又是一年。这一年,我们看到过巴以战场上无家可归的孩子,见证过巴黎奥运会赛场上的拼搏,也迎来了新中国的第75个生日……这一年,我们讨论经济、讨论房价股市,在现实的磨...... -
书香跨界,探索多元——世界读书日特别活动推荐书单公布啦~
在喧嚣世界中,读书是一次悄然的返航,是心灵栖居的灯火。风闻社区与万千读者共赴文字之约,于百余本热荐中,凝练出12部年度之选,构成2025年度图书推荐。春深四月,世界读书日,......
最近更新的专栏
风闻最热
-
 1只同居不领证,新型婚姻正流行 评论 332 赞 6
1只同居不领证,新型婚姻正流行 评论 332 赞 6 -
 2女大学生哭诉一个月只有1500元生活费 评论 233 赞 5
2女大学生哭诉一个月只有1500元生活费 评论 233 赞 5 -
 4流浪小狗头中两箭,警方介入,有人称“浪费... 评论 156 赞 2
4流浪小狗头中两箭,警方介入,有人称“浪费... 评论 156 赞 2 -
5印度始终没有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最近对... 评论 142 赞 156
-
 6多名学生出操时被地面烫伤,学校发表扬信肯... 评论 102 赞 3
6多名学生出操时被地面烫伤,学校发表扬信肯... 评论 102 赞 3 -
 7体制内换电脑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医院一类... 评论 73 赞 17
7体制内换电脑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医院一类... 评论 73 赞 17 -
 8如何看待法拉利CEO称不追求车内安装多屏... 评论 67 赞 2
8如何看待法拉利CEO称不追求车内安装多屏... 评论 67 赞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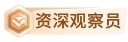








中国太大了,所以只要还有那些心气尚存,还在抵抗压迫的国人,那么他们就足以在多个方面甚至领域逐渐赶上、达到、超越世界一流。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被其他先进国家打压甚至暂时摁死的项目。但这些国家同样也是一样要靠十个指头来按压我们,当我们的项目足够多,他们压不过来时,就有一些项目能得以突破。而这些项目往往又能反过来给予其他被打压的项目鼓劲和支持,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说到底,这就像解放战争,蒋介石一开始搞全面进攻,后来搞重点进攻,再后来就只能搞重点防守一样。不是他不想持续全面进攻,而是他已经力不从心了。
所以,只看到客观存在的差距本身,和在看到差距的时候也看到有缩小差距的必然性,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就会有不同的想法。